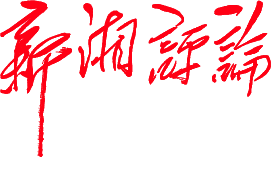我的一路都在循着父亲的脚印
爸爸于我是极特殊的存在。他驻外10多年,缺席我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但蓦然回首,我却似乎一路都在循着他的脚印。
因他的外派,我留学日本;因他的背影,我转身回国;因他是记者,我当上主持;因他的病痛,我学会了尽量坦然、尽力微笑……
他的远赴,我的成长
小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谁。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父亲就被派驻海外。
上幼儿园了,每当小朋友问我父亲在哪儿,我总会跺跺脚,“就在脚下,地球的那一边。”
上小学后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机场接一个叫父亲的人。一个胖胖的男人从里面一出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停,胡子茬儿扎扎的,好难受。我使劲推开他,放声大哭。妈妈赶紧哄:“他是爸爸!”“骗人,照片上的爸爸是个瘦子!”
这位爸爸的第一印象很糟糕,最糟糕的是妈妈从此晚上不再陪我睡了,我能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一种像火车跑过的声响。妈妈说,那叫“呼噜”。以前家里没有住过男人,自然不会有这么怪异的动静。一天我推开厕所门,看到爸爸站在马桶前,就十分好奇,非想转过去看看爸爸为什么要站着。爸爸急了,又不能马上走开。他用手挡着我,指甲把我的眼角划出了血。
刚上中学,父亲被派驻新华社香港分社,随后又派往驻日本的分社。
1990年,17岁的我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开始留学生涯。为了赚够学费和房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扫厕所。每晚六点半,我准时把18层大楼的每个男女厕所清扫一遍,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边的屎尿擦干净,让它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这样干了三个月,我又换了份餐厅洗盘子的工作。由于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并开裂。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洗盘子让我学会了坚强。
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有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决定要去日本留学时,妈妈没敢告诉父亲。当时在国外工作的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职务便利之嫌。后来真有人告到总社,说父亲把女儿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得以了结。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早已是人性化管理的必备福利,但当年,我不仅童年和少年没有父爱,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就在父亲身边,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经济上我更不敢伸手要钱。当年父母工资很低,随父亲出国的妈妈属于“编外”,每月工资很低。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和父母却极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父亲情绪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拼命赚钱的目标。
感谢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意志和赚钱的能力。女孩要对金钱、物质、欲求有足够自制力,要为自己未来负责。不论是扫厕所,还是洗盘子,我始终怀有良好的愿望与梦想,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体验。
爸爸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从总统、首相到老百姓、街头女,采访过无数人。当我成为记者后,遇到心中不平事,便会请教他。爸爸说:“记者应该触摸到最真实的世界,那里不全是阳光,还有暗影,这就是成长……”
他的背影,我的转身
199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妈妈病重。第二天,当我赶到北京铁路总医院时,已近黄昏。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我心急火燎地顺着楼梯往上爬。
突然哐当一声,吓了我一跳。抬头朝上看,只见在楼梯转弯处站着一个胖胖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提的两个铁盒掉在地上,饭菜倒扣,盖子摔下几级台阶,汤汤水水顺着楼梯淌下来……
他太胖,爬到5层已是满头大汗。他费力地弯下腰,很努力地挤压着肚子上的肉,用双手把地上的饭菜捧起来,放回饭盒里。油腻沾满手,他掏出手帕,擦擦手、擦擦汗、再擦擦地,然后把湿湿的手帕塞回裤兜,又下几级台阶,捡回盖子,装进塑料袋里。他直起腰,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扶着楼梯把手,开始继续向上爬。爬几级台阶又停下来,掏出那块油油的脏手帕擦汗,白背心已被浸透,前胸后背全贴在身上。
我一声没出,一动不动。望着那拎着饭盒、迟缓向上爬楼的背影,我眼里已满是泪水。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此刻,他如此苍老、如此尴尬、如此无奈。
想来父亲不愿在此刻被女儿看见,我隔着一段距离悄悄跟在他身后。他走进一间病房,俯身对躺在病床上双眼蒙着纱布的妈妈低声说:“瑞云,对不起,我上楼时不小心把饭弄撒了……”妈妈轻轻安慰:“没事,我不饿。”看着这般无奈,我拼来的荣誉、挣来的钱,又有何意义?“妈——”张嘴那刻,已做出决定:“我要回国。”
父亲很赞成:“我马上就退休了,你回来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再说媒体这行,还是把根基扎在自己母体文化上最牢靠。都在有为之年,何不早回来,把精力用于有用之所呢?”
这是老“新华人”的厚望,父亲的叮嘱。
他的病痛,我的坚定
2003年、2004年、2006年,这三年,父亲经历了三次大手术,三过鬼门关。
2010年春节后,父亲又住进了医院。父亲生病这8年,是我与他最亲近的8年。
父亲病了,他的同事、当年一起派往拉美的吴永恒叔叔来看他。吴叔叔向我说起当年的事,我才第一次知道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3年初,周总理决定由新华社派出5名记者组辗转到拉美地区未建交的国家进行调研,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朱荣根。1月4日,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等同志在晨曦中冒着严寒到北京站为记者组送行。
根据计划,记者组要访问11个拉美国家,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拉美是陌生的世界。当时,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都没想到,这次出访持续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在这次访问中,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在巴拿马举行的安理会会议。其间巴拿马外长胡安·塔克同意中国在巴拿马建立新华社分社。于是,总社马上决定朱荣根和吴永恒两位同志留在巴拿马,创建新华社分社。
从此,在接下来的5年,也是我童年大部分的时间,爸爸住在旅馆,出入受到“台湾使馆”和当地军情处的严密监视。当年,新中国举着革命大旗,“斗争”每时每刻都在身边发生。时局紧张时,窗外枪声阵阵,爸爸和吴叔叔只能憋在房里,等到吃饭和发稿时才下楼。爸爸和吴叔叔不能打电话,信走国际邮路,与家人天各一方,几个月才联系一次。孤独、寂寞相伴着坚守,回家遥遥无期。每天晚上拉窗帘时,才意识到又熬过去一天。
在巴拿马期间,两位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一起执行了无数次“特殊”任务:营救、传递、惊险……曲折、命悬一线。当年,华侨自动充当他们的后盾、耳目及保护伞。华侨说,这两位记者是“中国和巴拿马关系的开荒牛”。
在巴拿马时,父亲月工资30美元,吴叔叔20美元,他俩用每月50美元的工资开创了新华社巴拿马分社。从这两位年轻记者每天经历的枪林弹雨、眼前飘过的金钱美女中,我明白了“发财请走别路,怕死莫入此门”。这就是信仰,这就叫忠诚。
我在国外生活了10多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0多年,做媒体的,总会接触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名利权情、各种诱惑,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有人说:“让糖衣炮弹来得更猛烈些吧!把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去!”我说:“来不及了!炮弹定会直接炸在嘴里,炸得你毫无脸面。”
说完吓一跳,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
他的皮包,我的纪律
父亲在10多年驻外期间,也会偶尔回国述职。这难得的团聚,他最疼爱3个宝贝女儿。
那时,女孩子最馋的是冰棍儿。夏天,路边小推车里,厚厚的棉被下盖着三分的红果、五分的巧克力、八分的奶油雪糕、一毛二的双棒。买不起就在冰棍儿车旁站会儿,盖着冰棍儿的棉被掀开的瞬间,甜甜的清凉就已经能让我们美上好一阵儿了。
妈妈管着家里的钱,因为有3个女儿,还有姥姥奶奶要负担,每月过得紧巴巴的。但父亲疼女儿,发了稿费就会给孩子们带回几根冰棍来。为此,父亲回家后,3个女儿把他团团围住,像小狗一样拿鼻子凑着包儿闻,只是谁也不敢用手去碰他的黑色手提皮包。
这是家里的规矩,父亲曾特别严肃地告诉过我们,包里有保密文件和保密本,拉锁拉到哪里都是有讲究的,他看看拉锁就知道有没有人动过他的包。那个特殊年代,这就是铁的纪律。从父亲严肃态度中,孩子们明白:纪律就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有一次碰了他的包,那里面就永远不会有冰棍了。
家是个讲情不讲理的地方。爸爸很少命令孩子,而是用鲜活的言行影响着我们。这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20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父亲的皮包和那几根冰棍,冰棍早吃掉了,但父亲严守纪律的保密意识,全留在了我心里。
他的家训,我的护身
父亲是新中国派驻海外的第一批记者,他经历过很长一段中国被外国看不起的日子。他常说,国与国之间,实力就是硬道理。
2000年,我回国后,父亲天天叮嘱我两个字:“紧跟!”他不断重复:“紧跟政策,其他远离!”
父亲做了40多年的时政记者,常驻拉美时,那里的一些国家经常政变,他枪里炮里地采访着政权更替。之后,他又常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见识过各国政治家的高明手段。他赞叹之余,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碰这些,他只想女儿简单、幸福、快乐就够了。
父亲够,我不够啊。我刚回国,意气风发,光简单快乐哪够啊?一定要发展!当我回家向他抱怨什么时,他总是特别不屑,“没什么不公平的,生别人的气没用,别人成功是因为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努力着。”
父亲严格规定我回家的时限。我都20多岁了,除录像外,一定要回家吃晚饭,否则全家人就饿着等我。我被切断了所有应酬,不禁愕然:“您打小就没管过我,这是干嘛?”
父亲回屋,用毛笔写下泰戈尔的一段话:“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不要走错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的天职,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
10多年的起起伏伏,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不该是你的千万别拿,拿了是祸不是福。好好做人、踏实做事,老天爷看着呢……
深深凝望墙上父亲的照片,感恩父亲,这家训是女儿一生的护身符……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