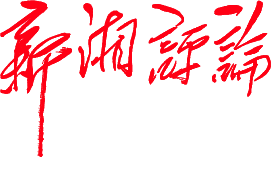计划时代(上)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他此行的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中国政府此前集中一批顶尖的经济行家,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结果拿给苏联征求意见时,苏方认为:它不仅不像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像。
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在经济运行中体现两个“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今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是因为无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明晰各自的优长和短处,拥有特殊的经验和体会。
经济计划是怎样编制的?
向苏联学习搞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计划,眼前的事实是,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过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便迅速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积累了物质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较好地执行了战后复兴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大大超过战前水平,重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相应,联合国也一度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推崇计划经济,是理所当然之事。
就新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显然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通过计划体制,采取高积累机制,集中配置资源,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则是务实可行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的两大政治优势,即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领域自然延伸。再说,新中国成立几年后,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用计划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实上已开始逐步实行起来。
为了尽快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领导层在干部配备和机构设置上,花费了很大心思。陈云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计划制定工作,他的副手李富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奉调进京,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6年,又增设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和编制。计划工作和计划机构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
在新中国,率先实行经济计划的,是重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四面八方的优秀干部和大学毕业生被选配到东北工作。1951年夏,23岁的朱镕基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他的直接上司袁宝华处长,后来长期担任国务院经济部门领导。东北工业部当时约有10个处室,计划处是最核心的部门,人数最多时达到180人。
有了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人才配备,还有苏联的帮助,制定经济计划看起来应该比较容易。然而,当新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真正做起这件事时,却发现困难重重。
最先碰到的问题是专业人才准备不足。政府体制内真正能够打算盘、看图表、找资源的人才很少,矿产资源的调查资料更为匮乏。
搞经济建设计划,重点是搞工业建设的计划。什么是工业?陈云的提法很有意思:“戳穿西洋镜来说,工业是一个叫‘地下’,一个叫‘机器’。”“地下”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地下资源的勘察与开采;“机器”最基本的是工作母机,地下掘出来的资源要靠机器来加工,才能成为工业品。
机器制造本来不易,要把地下的资源找出来就更难了。旧中国留下来的地质专业的毕业生只有200多人。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时,国家培训和调集的技术人员也只有1000多人。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这点勘察力量太小了。同时,进行矿产普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资料很难整理出来。旧中国留下来的有关地下资源分布、储量、构造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当时,苏联对寻求帮助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没有拥有地质资源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许多多的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你们怎么建工厂呢?”
不仅地质人才和资料匮乏,统计人才的情况也不乐观。据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当时苏联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品有3000多种,中国只有300多种,其中只有30多种有统计资料,其余都是参考有关资料估计的。为此,国家计划委员会就要求统计局增加统计报表。由于要求过高,一时报不上来,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之间就常常发生矛盾。
这就是当时中国开展经济计划工作的实际水平。
那么,制定经济计划的具体流程又有什么要求呢?今天的人们对下面的描述或许会感到惊讶。
中国采用的计划方法是主要产品平衡法,这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以女性必戴的发卡这种产品为例:做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对全国妇女的发卡用钢情况进行测算。近6亿人口约有3亿女性,除了小女孩以外,成年女性都需要发卡,一个人需要几对发卡,换算成需要的钢铁数,由此确定生产发卡需要多少吨钢。以此类推,当各行各业都计算出需要多少钢铁后,海量的信息汇集到国家计委,形成一个钢铁生产计划总量。随后,又根据钢铁生产总量的需求,来计算需要多少煤、多少电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了各行各业工业品生产需求的总数后,接下来就要计划需要增加多少工人和城市人口,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保障,等等。
由于计划各参数之间互相影响,如果其中某些参数发生变化,原定计划就要重新制定。比如,实际生产中一旦钢的产量达不到,其他都跟着削减;如果钢的产量比较多,其他相关产品也要相应增加。于是,有些地区和部门,直到当年的12月,还在修改这一年的年度计划,被人们戏称为“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
编制计划就像小孩子搭积木一样,稍有不慎,一块没有搭好,就可能导致整个积木坍塌。当时编制计划的作业方式,主要是打算盘、手工画表,一旦某个数字错了或者漏了,接下来的计划表格就全都不准确,必须重新计算。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国营天津酒精厂产品比较单纯,但作起生产计划来却不那么简单。学自苏联的计划表格很复杂,单是成本计划就要填报235栏,347项,6239笔。这些数字,需要3个人计算半个月,还得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才完成上报任务。厂子不论大小都采用一样的表格,这对于人数少、管理手段落后的工厂来说是吃不消的。
从宏观上看,编制经济计划采取的是上下集合的办法。1952年颁布的《人民经济计划编制办法》的规定是“两下两上”。先由基层提出编制计划的建议数字,上级机关综合平衡后提出编制计划的控制数字;基层接到控制数字后,根据生产实际编制计划草案,上级机关经过讨论和论证后,最后批准和颁布计划。
新中国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对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李富春当时做的解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他说: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和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改造;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保卫祖国的军队,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也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个解释,事实上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实现工业化问题上积淀的历史感情和经济逻辑。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共施工了921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其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是重中之重。1953年,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下线;1955年,第一块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第一套6000千瓦发电机组在上海组装;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武汉建成通车;1958年,“东方红”牌拖拉机制造成功……
中国的工业化,在短短五六年间,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建立起钢铁、航空、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拖拉机、化学药品、发电设备、矿山设备等产业部门,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实施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原子能等高端工业部门,现代工业体系更加完备。
老百姓的吃穿用
1963年3月17日,中国乒乓球队即将赴布拉格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家里做客,同时还请来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邀请大家时附了一项特别申明:吃饭的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支出,但参加宴请的每个人却必须自己掏粮票。
在那个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每个城镇居民都有自己的粮食定额和对应的粮票。总理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但每月领取的粮票与普通城市居民却是一样的,可以花钱请客,但无论如何不能花粮票请客。
城镇居民为什么要用粮票?它从哪里来?
民以食为天。由于人口众多,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从来被视为天大的事情。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宣称: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才会发生革命。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美国新闻记者替他说出了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将不可能稳定。毛泽东批驳了艾奇逊的观点,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吃饭”的问题,完全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恢复很快。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3亿斤,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570斤。和过去相比,确实相当不错了。但由于当时肉、蛋、奶等副食品供应非常有限,一个人每年570斤原粮也仅是够吃而已。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基本建设投资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自由市场上的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推波助澜,粮食供应陡然紧张起来。
按照计划,1953年7月至1954年6月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只能收购粮食340亿斤,粮食供应任务量却增加到567亿斤,缺口达到227亿斤。
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主管这项工作的陈云,一笔一笔地算细账,想来想去,都是个两难选择。为什么说是两难?陈云的顾虑是: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硬行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农民不干,政府就可能挨农民的扁担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又势必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政府不得不拿出紧缺的外汇到国外进口粮食,就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国家发展不起来,最后农民还会用扁担打你。总之,“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推进工业化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双重困境中,陈云先后设想了八种方案,供粮食部门讨论。权衡利弊,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只能是“又征又配”,即向农民征购,向市民配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陈云提出的方案,毛泽东最后表示:征购配售,统一管理,势在必行。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一是农民不满,二是市民不满,三是国外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当时担任粮食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建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
还好,1954年开始搞统购统销,比较顺利地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势。这项在短缺经济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国大陆实行了将近40年。
今天的年青人对此已经很陌生了,在过来人的记忆中,统购统销是同农民交售公粮、城镇居民用粮票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城镇居民每月大致有30斤左右的粮票,根据职业、年龄和性别,有些微差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多一点。如果出门办事,在本地区用地方粮票可进饭馆吃饭,跨地区则必须用全国通用粮票,粮票由此被老百姓称为“第二人民币”,光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
其他生活品的供应,也先后采取了票证制度。比如,买布做衣服,则使用配额的布票。布票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逢年过节给大人或者孩子换一身新衣服,是件大喜事。孩子较多的家庭,对“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这种生活经历,记忆非常深刻。除了粮票、布票,还有油票、肉票、糖票。日用轻工业品方面,肥皂、火柴、自行车、手表之类,也先后凭票供应。
票证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从根本上说,与短缺经济时代有关。放眼世界,在食品供给上实行票证配给制度,确也不是新中国首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军队占领后,食品短缺,维希政府便从1940年开始对面包、红酒、食糖、牛奶、肉类、食用油乃至巧克力、咖啡、水果蔬菜等几乎所有的主要食品进行限购,进而把国民分成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重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农民以及老人等不同的档次,实行定量配给。战后的法国,依然无法立刻结束食物配给制度,直到1950年代才彻底摆脱定量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用品的供应较之从前大大增加,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3300多亿斤增加到3900多亿斤。1956年棉布供应达到17365万匹,其中民用布为14948万匹,相当于1949年市场供应量的3倍多。为什么粮食、棉布的产量增加了,市场供应仍然紧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仅从1953年到1957年,便由5.87亿增加到6.46亿,在此后相继达到7亿、8亿、9亿(这也是在1970年代开始逐步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票证制度能大体保障人民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从社会需求来看,实行票证制度,因定额有限,不能使人们的购买意愿全部实现,限制了货币购买力,但同时也弱化了消费膨胀对经济的压力,也弱化了对市场物价的冲击。而且票证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定向发放,分配基本公平,能有效地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现在,人们把这种生产生活的安排方式,叫作高积累、低消费。正是靠着全体老百姓勒紧裤带过紧日子,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仅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担负抗美援朝战争巨大消耗的同时,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8亿元,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6亿两黄金。工业方面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100年的投资总和。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看到了这种计划体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意义。他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更快。”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