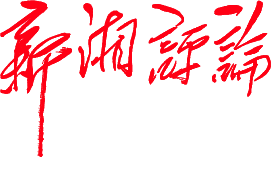绿萝绿萝你别走
满卧室的植物,发财树、白玉兰、红掌、多肉、文竹、菖蒲,一个一个死光,唯绿萝还活着。
像一切通俗故事那样,最不起眼的挺到最后。草根逆袭。
我把赤橙黄绿各种植物挨个儿搬回家时,花店老板慷慨地说,再搭给你一盆。
绿萝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参与进来的。
卧室里盛不下姹紫嫣红总是春。地位最低的让路,绿萝避居阳台。岳父在阳台上种菜。彩椒、香菜、臭菜、小白菜、黄瓜等,是岳父放牧的“羊群”。观赏为主,偶尔摘下来吃。阳台挤得特别满,植物们半夜为了争地盘站起来“吵架”。岳父哄了这个哄那个,好不容易摆平,又加进来一盆非我族类。
某一天我往阳台里瞅了一眼,绿萝上面布满灰尘。我所居住的城市空气清新,经常下雨。灰尘多,只能证明时间太久,让灰尘们有机会凝聚成堆。又过几天,绿萝不见了。问岳父,答曰,那不是假花吗?刚扔。这么久还绿着,以为是塑料的。我赶紧跑到楼下垃圾箱乱翻,居然找到。拎起一看,还真像塑料。没人管,没人养,应该蔫头耷耳,垂头丧气,它不,肮脏的叶片不服气地挺立着。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了生存规律。
正好卧室里一盆红掌离世。绿萝被擦干净,填补这一空白。
也不知是我不适合植物,还是植物不适合我,一段时间后,植物们或枯或腐。为它们送葬完毕,面对着孤独的绿萝,黯然神伤。曾经多么热闹,转眼就“零落成泥”。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也就三四个月时间。绿萝没心没肺地看着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精心擦拭它,培植它。把全部心血倾到绿萝身上。它的叶子真绿,油汪汪的绿,但是真脏。花盆里的土不知不觉掉下来,有的是被浇花的水冲入底座塑料垫中,再溢出来;有的是挪动时落到地板上。那点土,放在广袤的大地上什么都不算,在屋子里就显刺眼,还要收拾。人矫情,土壤没有立足之地,毕竟还有更干净的方式,即水养。
水养最省事。朋友告诉我的。
我收集了各种瓶子,把盆中独立成枝的绿萝一株一株撕下来,插进瓶子里。
太爱这些瓶瓶罐罐,个个像艺术品。我一度痴迷之,总能从它们工业化的造型中找到不平凡。它们的漂亮只是金玉其外,必须和“其内”共进退,即便“其内”是败絮。它们身世非凡,曾经装过药,装过酒、蓝莓汁、小吃、茶叶、干果,等等。“其内”用毕,包装扔掉,被保洁员捡起卖到废品站,粉身碎骨,从头再来。现在省略了这些环节,它们直接获得新生。透明的,不透明的。玻璃的,塑料的,陶瓷的,不明材质的,装上水,微波荡漾,便是精雕细琢好风景。
掰下同样大小的两枝绿萝,一枝放进大瓶子,一枝插入小杯子。过些时日,大杯子里的突飞猛进,围着杯子扎一圈绿篱笆。若见过它初时的样子,绝对想不到它会长这么大。是瓶子怂恿了它,跟它说了悄悄话,做了大包大揽的许诺。绿萝不再犹豫,奋力而为。小杯子里的那枝,自动缩身。杯子可能什么都没说,绿萝自己感到了危机,不声不响自我调整。
杯子圆,它们圆。杯子方,它们方。它们不做突兀的事。不硬抗。先迁就离自己最近的容器,再融入周围大环境。绿萝互相之间并没沟通,入乡随俗是它们共同的,与生俱来的价值观。
一个花盆里的绿萝,越分越多。我把它们摆在卧室的各个角落,再蔓延至书房、客厅、洗手间,以及厨房。厨房里的那一瓶后来被妻子挪出来。她说那里烟气太大,不利于绿萝生长,其实妻子视其为潜在危险,担心不小心撞倒花瓶,扎了手脚。
植物的命运走向,因它们完全不知道、想象不到的理由而被进行各种选择,除了听之任之,似乎也没办法。
绿萝在我的家里奔走。有的快跑,有的慢跑,有的爬行。它们的姿势貌似定格,殊不知第二天便小幅位移。三天两头换个面貌。它们大的大,小的小,竞相开放,互相补台,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风景园。直到我把最后一条绿萝连根拔起,洗干净,插进一个笔挺的玻璃瓶里。花盆扔掉。
看过一个视频。演员站在舞台正中央唱戏,镜头扫过每一个伴奏者,长久停留。那些拉弦的,打鼓的,敲锣的,每一个都青筋绷起,肌肉颤抖,超大的动作幅度,表情随剧情和动作随时变换。台下的观众看不到主次,眼神瞄到谁,谁就是主角。恰如满室绿萝,嫩绿、深绿、浅绿、明朗的绿,暗淡的绿,迸发着姿态各异的生命力。
还有我看不到的,它们净化了空气,并释放我需要的氧气。
如果我懒,可以不用给它们换水,适当加水即可。有时不注意,只剩一寸水在杯子底部。绿萝褐色的细根紧张兮兮地捏着那点水,生怕被夺走。上面的枝条和叶片则东张西望,似在找寻其他出路,又似在呼救。我倒一缸子水进去,它们集体大喘气,安静下来。绷起的叶子舒展开。这样的情况并不多。闲时浇花,和一株绿萝对视,乃生活常态。它们应该比我更有安全感。
也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从生到死,从稚嫩到苍凉,体态发生变化。绿萝呢?气候适宜,有源源不断的水,它们会不会死?如果不死,我就得照顾它们到老。它们可能活得比我还长。如果死去,又是怎么个死法。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天灾,还是自然死亡?
某天早晨,看到一片叶子悄然枯黄,确定不是病虫害。
我心里踏实了,把它从晶莹的广口瓶里捞出来,扔进垃圾篓。一片叶子死掉,就会有第二片叶子。第三片和第四片。根须由褐色变苍白,粗壮变纤弱。
绿萝创造的再度繁荣,也因为有了退出机制而趋于萎缩。瓶罐里的成长总会遭遇天花板。它们适应了瓶子,瓶罐呵护了它们,成就了它们,也限制了它们。它们在瓶子里长大,却无法分蘖,枝条上没有新的叶片生成。叶子枯萎一片就少一片,再无增加。
当一半的绿萝变瘦,瓶瓶罐罐扔掉一半,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下去,它们和最先离世的植物们除了死法不一样,也没什么不同。我早晚将像失去红掌一样失去绿萝。
我买回一个大花盆,从路边挖了一点土,把水瓶里的几根绿萝挪回去。
回归真是痛苦。我能看出来。毕竟已适应了自来水的环境,干净和孱弱。根须被强行插入土中,绿萝挣扎着要跳出来。像不会水的人在大海里扑腾,叶片扭曲,时枯时荣,抓住盆沿儿摇晃。土壤里的元素每次以新的方式进入它们的身体,都带给它们撕心裂肺的痛楚与喊叫。
土壤包围着它们,并无陌生感。见多识广,曾经养育过万千植物的土壤,对谁都没敌意。它安抚着绿萝,仿佛抚摸失散多年的儿女。慢慢让它们恢复了平静。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
逐渐地,叶片恢复了生命的油亮。嫩芽悄悄从叶片的腋下钻出来,一朵接着一朵。慢而坚定,不可阻挡。
土壤中的绿萝越长越大,遥望着不远处水瓶中的绿萝。
在水中,绿萝的长大就是死亡。死亡紧追着死亡。在土地里,绿萝不断滋生,根须蔓延,叶片更新。它们的死就是生。生就是死。水中没有轮回,土壤里有。
有了它们,我就不担心水瓶中再无新生命到来。轮回与消亡并行。我的卧室里生机一片。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