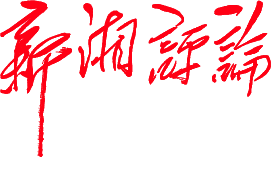文章为美而写(下)
——关于《天边物语》的审美絮语
本期音频由《新湘评论》“青年党员读党刊”活动协办单位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民族中学提供,朗读者:肖存。
8.趣味是什么?
美在“三境”之外还表现出一种趣味。这可以溯源到人的味觉功能。将生理的味觉上升到心理的感觉就是心头的“滋味”。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一种情绪的审美。李泽厚在《华夏美学》里说“在中国,美这个字也是同味觉的快感联系在一起的。如钟嵘和司空图关于诗歌的著作,还常常将‘味’同艺术鉴赏相连。”
趣味是主体以外旁生横逸的东西,是溢出河面的小溪,是花朵周围的暗香。在人是幽默,在事是含蓄,在诗歌是比兴,在绘画是写意,在文章就是趣味。一件事物如果总是规规矩矩,就枯燥;一个人总是正襟危坐就呆板。人与物总要生出一点另外的东西才可爱。苏东坡说“竹外一枝斜更好”,李商隐说“留得枯荷听雨声”,都是竹林、荷叶常态之外的东西,是旁生横逸之美。趣味是弦外之音,是美意不经意间的流露。在书中,《一树成桥》错中成趣;《鬼子与老子》神秘之趣;《芝麻开门,柿子变软》微妙之趣;《路边一只石老虎》童真之趣;《这里有一座歪房子》反衬之趣,等等,都是主体外溢出来的趣味。梁启超一生事业波澜,著作等身,但他说,如果把他放在化学烧杯里溶化了,其实只有“兴趣”二字。序里说“物本无言,全在人悟,悟则有美,悟则生趣”。趣味是人凭借自己的理解从物中解读出来的美。如很少人注意苔藓这个最低等的生命。但在作者眼里它却是对人心灵的抚慰,充满情趣。“它抚摸着过去的时光,给每一件旧物盖上一层温柔。”贵阳郊外的一片草地,作者却联想到了草船借箭,想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见本书中的《人与草色共浪漫》)。书法家能从墙上雨水的漏痕中悟到笔意。只有对生活满怀兴趣的人才能感知趣味之美。
9.趣味与意境的关系
美达到形、情、理三境,已经美得够可以了,何以在美的大餐中又再加一道菜:趣味?境界与实物相比已是虚境,是人们离开实体而安放情绪的一个假设的摇篮,是一处虚化的地方。我们常说妙境、仙境、险境、绝境、幻境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虚,它还是一个“境”,一个环境。而趣味,则连这个境也没有了,进一步虚化成一种“味”——趣味,或淡或浓,缥缈不定,不能定于一处,不能止于一瞬。这种美感也只有拿“味”来作比了。境界从人们对实物的审美中来,趣味又从境界中生。境界是亦虚亦实的美,如果我们嫌其虚则进一步抽象为“意象”(如本书中《常州城里觅渡缘》的“觅渡”),意象是境界美的定格,可以虚拟地慢慢把玩;如果我们嫌其实,则可以抽象为“趣味”,趣味是境界美的发散,可以虚拟地闭目品味。如果把审美对象的意境比作水,水凝则为冰,冰清玉洁,一个美丽的意象;水蒸则为气,氤氲蒸腾,一种笼罩四周的趣味。
趣味可分为情趣与理趣。由情绪而生的心旌荡漾,浮想联翩之美为情趣。由思考而生的研究之心、求知之欲的美感为理趣。不管情趣还是理趣,都是由审美对象决定的。如墙上探出的一枝芭蕉花很像一支大彩笔,这是情趣。它天生奇特,不必问为什么。而一片海芋叶子,让虫子十分规则地吃成一个筛子状,就生理趣,人们不禁要思考其中的道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情趣,“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理趣。桌凳于地可能四脚不平,可用小木片来垫,这是常事。但是宋代诗人刘子翬却说:“不是乖绳墨,人间地不平”,这是理趣。自然界随处都有趣味。
趣味又分高级和低级,这关乎审美者的知识道德修养。有时名曰审美其实是审丑。
10.视觉第一,联想生美
在我们的五官中眼睛是最重要的,有人研究,我们得到的知识75%以上来自眼睛。那么人的美感由视觉而得之者也应占多数。除了声音之美靠耳朵的捕捉,绘画、雕塑、戏剧、电影、杂技、模特、健美等一切表现、表演艺术都靠视觉感受。湖光山色更是让人大饱眼福。王勃的《滕王阁序》借景抒发惆怅之情,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讲心忧天下的大道理,却从大段的风光描写入手。“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说明感情的酝酿,常常是从眼前的景物开始,即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由“形”而达情及理。
我回忆自己的第一次审美启蒙是小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精美玉制工艺品的大画册,买回家去每日翻看不倦,从此喜欢收集养眼之物。鲁迅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题诗:“聊借画图怡倦眼”。可见好的图画可以怡抚倦眼,愉悦人的心情。本书大量采用图片,全书152页,共用了69幅图,就是为增加视觉冲击。虽不能看到现场的实物美景,但通过图片转换仍会“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油然而生美感。
美感产生于视、听、味、嗅、触等各种感觉产生的联想。根据相似学原理,事物间都有相似点互通,这是修辞比喻的基础,也是审美联想的前提。如说“她笑得像花一样”,人笑起来,脸部线条确实与花朵相似。书中所收图景在第一时间就曾使我心动。《秋色醉,旅人不须归》是秋天的一个早晨在婺源县宾馆看到满地色彩斑斓的落叶,我立即想到杜甫的那句诗“此曲只应天上有”,这块“地毯”只应天上有。这是视觉与听觉间的联想,也是由景到诗、到画的联想。在此书将要付印时,我在贵州的一个溶洞里看到齐腰高的一根钟乳石,竟然已有40万年,立即联想到6年前在江西竹林里见到过一节同高的竹笋,却是一夜长成。这是跨时空的联想,于是翻出旧照同框刊出,相信这种视觉冲击一定能让人感到时间的魔力,宇宙的永恒。视觉之美,由耳目入脑,如种子落地,十年、几十年,有时一生也不会忘记。
这69幅图中除大部是摄影外,有两幅是我的画作。在野外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本来看到激动人心的一棵树,一处景,收到镜头里却很平平。因为人眼所见是经过目光过滤,大脑处理后的形象,优于镜头的机械抓取。这时就不如亲自动手去画一张。如《一棵改写了历史的老樟树》,在照片中树与房齐高,并肩相连,而在绘画中则古树横空出世,尽显它的高大,而房子却很乖小,更不用说房子里面的人了。是为诠释自然的伟大,再大的人物也逃不脱自然的庇护。画比照片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思想。
11.文章字面的音乐美
文章不是直接的视觉、听觉,只能间接转换它们的美感。作为纸媒,视觉美可以通过插图来帮忙,而听觉,只有靠字的发音。所以读书要高声朗读,诗歌更要朗诵。前面说过汉字是由形、声、意组成,这个“声”就管文章的音乐美。
音乐美在文字中的体现是韵律和节奏。诗的韵脚除了产生声音的美感还有节奏作用,就像民乐中的鼓点、戏剧里的梆子。它是声音同时也是节拍。一句、隔句或长短句的押韵,就分出节奏的长短,产生了语气的急切与舒缓。本书以文为主,但杂用了诗词曲赋,就是为表达不同的情绪节奏。古体诗情绪饱满节奏严整:“人欲微醺半杯酒,天地要醉一夜秋。层林尽染五花马,红叶披挂百丈楼。”(见本书中的《不如面对一院秋》)词就自由跌宕些:“立为一棵树,倒是一座桥,桥下流水东去也,桥上行人早。一任众人踩,无言亦不恼,更发新枝撑绿伞,伞下儿童跑。”(见本书中的《卜算子:一树成桥》)。而曲子来自舞台的唱念,节奏口语化,更显自然、诙谐、活泼。“那果儿,如灯盏引路,亮晶晶。那叶儿,如柳眉低垂,羞答答。不声不张,自是惹停了多少车马。”(见本书中的《路边的钉头果》)至于赋则是从有韵文到无韵文之间的过渡,韵脚已显随意。韵律的回环与节奏的交替似断还连,就有了乐声隐约的美感。“虽军情火急,院门吱呀,不废房东荷锄归;指挥若定,读罢战报,还听窗外磨面声。一战而取辽沈,二战而收淮海,三战而下平津。全国解放,大局已定。”(见本书中的《西柏坡赋》)大体上各种文体的音乐节奏感是按这样的顺序由严整到散漫,渐趋舒缓、随意:旧体诗—词—曲—新诗—赋—文。闻一多说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这“镣铐”就是乐律。白话文是彻底没有了镣铐的,也就少了乐感,所以有时我们仍愿重戴“镣铐”,借助诗词曲赋的形式再找回一点乐感。只要留心,就是在散句子的白话文中,语言仍然可以利用声韵,用调整单音或双音词等方法,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暗存乐感。这说明文章与音乐还是有天然的联系。
我曾经说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而这本书专门是为美而写的。
路边的钉头果
2018年11月7日,我在云南宾川县的一家路边小饭馆吃饭。门口一小树,枝很细,叶片如柳眉低垂。上面结着十几颗泡状圆球,乳黄色,半透明,如网球大小。球面布满发丝细的小钉,因此就名“钉头果”。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植物,不知该称它是花还是树,也不知这些个泡泡是花还是果。问主人原来是一印尼归国华侨,此木原产热带之非洲。门前种此,是借物之奇,为饭馆招揽客人。果然,食客多“见果下马”,落座就餐。我出于好奇,便摘了一两个干果带回北京。又顺寄新疆朋友,托其育种,第二年出苗,装盆,托人经西安缓存半月,我去开会时带回北京。已遍历大半个中国,经多种气候、海拔之催变、考验。如此大空间的调度,真像太空飞船育种实验了。苗在阳台上生长,五月初正当我生日那天开花,可见有缘。花白色,分泌液滴,甜如蜜。秋天枝头果然结有小灯球晃动照人。现已移到室外,郑重赠送给园林队。这大概是该品种北京引进之第一例,“独在异乡为异客”。我突然想起苏东坡叹柳絮的《花非花》,作打油诗一首:
是花还是非花,也无人去管它。
秋阳高照,风过处,轻摆枝丫。
举灯泡无数,轻如气球,圆似乒乓。
又薄如蝉翼,嵌百千细钉,密如麻。
问主人,原是为作一个招客的酒帘挂。
你看它垂手路旁,
引客回眸,闻香下马。
那果儿,如灯盏引路,亮晶晶,
那叶儿,如柳眉低垂,羞答答。
不声不张,自是惹停了多少车马。
宾川在滇西北,属大理州管辖,知道者不多。但它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境内海拔有上下7000米的落差,立体气候最适合生物多样化,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温带到热带,所有植物在它这里都能安家。回京后,我因这钉头果一缘,顺势写了一篇《秀色可餐在宾川》发在《人民日报》上,未想被好事者看中,入选了2019年的全国语文高考试题,无意中为该县作了一个免费广告。县里大喜,专门发文宣示全国,凡本年考生,一律可免费来宾川一游。
(摘自《天边物语》)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