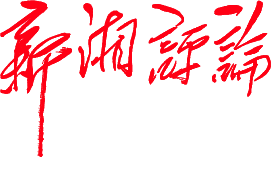伟人之初
——毛泽东是怎样被历史选择的(三)

为中国革命寻找根基:走向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早在1922年7月底,他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海丰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后来又担任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他1926年初公开发表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影响很大。毛泽东称赞他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1922年开始组织农民协会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党内注意。那时,全党都倾注心力搞工人运动,甚至分不清彭湃的农民运动和陶行知提倡的乡村教育有什么区别。比如,恽代英当时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1923年2月7日,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毛泽东见事早,反应快,意识到孤军奋斗的工人运动,难以成燎原之势,应该寻求更多的同盟,比如农民。这年春节(2月16日)过后,他在长沙清水塘就要求前来谈事的水口山工人运动领导人刘东轩,赶快回家乡衡山县白果开展农民运动。
有此转念,毛泽东在这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明确提出要“注意农民运动”。三大由此通过了他参与起草的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那时,中共工作的焦点是国共合作,搞农民运动还不是当务之急,包括毛泽东本人,事实上也无暇顾及。真正让他意识到必须而且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的契机,是1925年在韶山的半年农运实践。而此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却已经开始下降,与陈独秀的分歧也显露出来了。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同时也向中共中央请假“回湘养疴”。此时,他负责筹备的中共四大召开在即,此番一去,结果在四大上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毛泽东后来说,他是逢双没有参加党代会,即二大、四大、六大没有参加。二大原本得到通知参加,但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找到开会地址错过了。四大理应参加,但不知何故,毛泽东硬是以养病为由离去。结果是,不仅失去了中央局委员职务,连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四大选出的中央局委员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上苦斗,确实无法参会,但井冈山毕竟已经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然而毛泽东依旧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四大上离开中央,虽说是个遗憾,却也算不得什么挫折,何况他当时受中共派遣在国民党内工作,并没有影响他的才干发挥。
借养病之机,毛泽东得以开辟他三大上就已提出的农民运动新实践,果然闯出一片新天地。他在家乡农村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并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组建起国民党区党部,配合五卅运动,建立起20多个乡雪耻会,口号是“打倒列强,洗雪国耻”。韶山农民运动的高潮,是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的斗争。7月间韶山一带遭受大旱,青黄不接之际,成胥生乘机囤粮,抬高谷价,毛泽东派人去交涉,遭遇拒绝,成胥生还偷运谷米到外地卖高价。毛泽东果断发动四方农民前往阻止,逼得成胥生开仓平粜谷米。其他地主也不敢再囤粮卖高价了。
毛泽东在韶山一带搞的农民运动,惊动了湖南省长赵恒惕。他电令湘潭团防局急速抓捕毛泽东,毛泽东这才不得不潜回广东。
这段经历,让毛泽东很兴奋,对他在大革命后期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1925年12月他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我开始对陈独秀的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把这篇文章作为开卷篇,也顺理成章。他还为此文专门写了一个题注说: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呢?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从部长到所长,舞台虽然变小,但正是他兴趣所在,是他寻找革命力量的契机。
关键是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行行都搞得轰轰烈烈。除自己为300多名来自20个省区的农讲所学员讲课外,还邀请了当时在广州的大批国共精英授课,编印出版了26种农民运动丛刊,组织师生到彭湃家乡和韶关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实际情况。毛泽东此时的一个鲜明主张是:“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事实正如所料。广州第六届讲习所学员结业后,大多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再度崛起的依靠力量。其中,来自湖南的第五、第六两届的学员多达80人左右,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与此有关。毛泽东后来率部上井冈山同袁文才会面,就是当时在袁的自卫军里做事的一位叫陈慕平的农讲所学员牵的线。
当时,中共的主要精力,还是立足于城市和工人运动。党的早期骨干,张国焘、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王荷波等都投入工人和市民群众的发动。开展农民运动,主要是借助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这块牌子。1926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又在武汉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并主持武昌中央农讲所。这时候,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实际上兼具国共双重身份,说他是两党的农民运动权威,是全国农民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也不为过。这段时间,他确也是煞费苦心地推进农民运动,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目前农运计划》,为推进和深化全国农民运动作整体部署。
国民党上层此时还没有放弃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也乐见北伐军所到之处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和配合。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的核心层人物看来,农民运动并非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不是主战场,只属于可借重的“偏师”。更重要的是,打倒军阀和扶助农工毕竟是两回事。在国共之间,反对目标的一致,并不代表建设目标的一致,革命对象的一致,并不代表革命目标的一致。国民党要打倒的是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及其政府,并不在意这些军阀及政府得以形成的半封建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共则不同,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打倒北洋军阀,还要推倒其立足基础的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并且认为,只有让工农翻身解放,才算是国民革命的成功。这种潜在的根本分歧,使大革命深入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国共分裂,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由大大小小的“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势力,是不可能允许农工翻身抬头的。
遗憾的是,身处局中的中共领导层,当时很难看清这样的历史逻辑,由此陷入困局。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政坛上,好不容易有了中共的一席之地,又有鲍罗廷这样的苏联顾问在上面驾驭着大革命这艘航船,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一切以国共合作为要,也许是情理中事。于是,以为埋头去动员群众,真心实意地去扶助农工,以配合北伐战争,这便是对国民革命的最大贡献。问题在于,就是这样去做,常常也要看国民党的眼色行事。比如,当工农运动狂风暴雨般兴起来以后,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且掌握实权的国民党右派,包括一些北伐军官,坐不住了,攻击工农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扰乱了北伐后方”,中共领导层也慌了手脚,觉得工农运动确实已经“日渐向‘左’”了。
毛泽东1926年12月一到武汉,就碰上了党内的争论。他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与会者多数不同意陈的意见,毛泽东赞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更好地发动农民,同时提出“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是他和陈独秀第一次面对面的政策交锋,似乎还敏感地触摸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在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的思考是成熟的,也拿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陈独秀的观点。他稍后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分歧明显加深了,但他当时仍然很尊重陈独秀,在引导中央决策上还不是那么自信,也“无由反对”。最后,这次会议作出决定:限制工农运动发展,换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由右向左”,扶持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这个决策,自然很难达到目的。国民党内确实有以蒋为代表的“右派”和以汪为代表的“左派”之分,但左派中除少数人是真心实意要和共产党合作外,大部分和蒋介石之间是权力之争,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支持,不过是加持他们分量的砝码而已。
怀着疑问,毛泽东决心到实地看看农民运动是不是“过火”和“幼稚”。1927年1月4日开始,他历时32天,深入湖南5个县考察农民运动实际情况。回到武汉后,他就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自己在湖南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武汉、长沙城市里的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直陈中央的农运政策有误,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结论是“农运好得很”“贫农是革命先锋”。在随后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具体描述了湖南农民做的14件大事,孙中山搞四十年革命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这篇报告却受到中央的冷遇,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被陈独秀、彭述之砍掉,不让登出来。担任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不干了,气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当即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言,让人赶快排印出来,出版单行本,以广传播。瞿秋白确实是眼光独到,在序言中明确讲,“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还称毛泽东和彭湃是“农民运动的王”。这个称号,一下子把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上的贡献放到和彭湃相等的位置上,对扩大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候,中央领导层政策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很活跃的,是蔡和森、瞿秋白,蔡是毛泽东的老朋友,瞿是毛泽东出席三大时结识的,二人都有深厚文化素养,相知甚深,都作为跨党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实际工作。在推荐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后不久,5月4日,瞿秋白发表雄文《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径直提出,中国革命已到“新阶段”,其任务是“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5月下旬和6月中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把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这大概是毛泽东比较早地进入共产国际视野的一个见证,当然,从布哈林省略名字而以“鼓动员”相称的口吻看,毛泽东似乎还不属于中共党内的重量级人物,那时,他在瞿秋白眼里是“农民运动的王”,但在党内毕竟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农民要求的政权和土地的主张,很让陈独秀头疼,陷入两难。广大农民和像毛泽东这样的农运干部要求实行土地革命,而大多数地主家庭出身或与土豪劣绅关系密切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一些北伐军官,又明确表示反对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要求则是,既要支持土地革命,又不能让国共合作破裂。因此,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和他的考察报告,“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与此同时,毛泽东热心在国民党中央层面同国民党左派互动,推动实现他的主张。为了打着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旗号推进北伐,在武汉的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央土地委员会,毛泽东是五位委员之一。开会时,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最后达成一种妥协,为适应农民的迫切要求,而又使国共合作不受危害,解决土地问题分两步走,第一步,搞“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这样一些“反革命派”的土地;第二步搞“经济没收”,即没收一般地主出租给他人的土地。这个妥协方案,最后也没有通过,汪精卫明确表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在全国统一之后。
毛泽东仍然不放弃。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五大期间,他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开会,搞了一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陈独秀甚至都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从此,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彻底失望了。他后来同斯诺谈到中共五大时的陈独秀,流露的口吻是:“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是在风云变幻的特殊局面中召开的。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还通缉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的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当时的选择,只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由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
蹊跷的是,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只是作为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的“候补代表”参加中共五大。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对毛泽东那么热心搞农民运动的看法,不言而喻。正式代表们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当选为14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一,而中央执行委员有31名之多。这样的结果,或许不能算是很公平的。五届一中全会还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其他人则分别担任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人部、农民部部长。担任农民部部长的是谭平山。 (未完待续)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