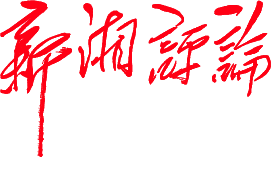鸟语花香里的酬唱

阳春三月,我们去湖南省植物园踏春,预约了两次,方得入园,可见广大市民胜日寻芳的盛况。
我与妻选择了植物园里一条冷僻的路。平阳处,几张长条凳,留住了树荫下小憩的三两对人。不时小语,不时发呆,然后离开。我和妻就坐在其中的一张木条凳上。
这时,一群声音冲耳而来,仿佛有蝉,细听又不是。可确定的,这不同于鸟声,是虫鸣,鸟语花香间泄出来的虫鸣。鸟语花香间有虫鸣?我疑心是幻听。我向妻求证,她说,是的,她也听到了。
于是,我们安静下来。这声音是成簇成团的,先是林子里的鸟声,再是林下水塘中的蛙鼓,轻远一点的才是叽叽吱吱的虫鸣。相对于鸟声的清扬,蛙鼓的浊重,虫鸣却显得郁抑闪怯,黏丝稀薄,不似夏秋虫那般锐利。渐渐地,我被这虫声吸住了。虫声,来自远处,又似在耳畔。疑在高处,似乎又就在脚下。虫声,此起彼伏,互相应答,又像是争吵着。不一会儿,这幽僻的空间里,便满是这种声音,连喧闹的鸟声也只是陪唱了。
我庆幸,竟然在这花鸟主场的春阳里听到了如此丰富的虫儿们的酬唱。这声音,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只虫发出来的,我也不认识它们,它们的身形隐在微观世界里,唯有声音在宏宇间证明着生机,装点并美化着世界。
本来,春虫在鸣,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只是,有秋声虫语的成语和习见在前,加之耳目所闭,人们没有把春日里虫的讯息作为重点。人们把注意力放在鸟的啭唱,花的芬芳上,至于虫的奏鸣就无意间被屏蔽掉了。何况,这时的虫们都是经过冬的蛰伏才醒来的老虫,或新生的幼虫儿,断不会像霸占秋声的壮虫那样骄傲而高调。
春天,空气里充满着荷尔蒙。花在受粉,鸟在求偶,连天上的云都在牵绊纠缠着。《诗经》上都说了,“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万物萌动,凭虫的灵性,不可能没有动静。在草叶间,我就看到了牵连着,叠叠着的虫儿们,蹁跹着的蝴蝶们。
一时间,我陶醉在“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氛围里,聆听着虫们的声音,清新而执着。
“嗡—”的一声,一只灰褐的甲虫急惶间撞到了我,然后弹落在地上。它仰翻着身子,用脚惊慌地划着,怎么也翻不过身来。显然,它被这次遭遇镇蒙了。我弯下腰去,用一根细干枝将它翻转背来,它迟疑了一下,爬行几步,慌张地看着我这个巨人,才又吱地一声飞入林丛。它的声息,融在了空气中,弥漫盘旋并放大着。
林间有一些开淡紫花的鸢尾、犁头紫丁,吐粉色,白色花丝的檵木,举着小绒拳的金毛蕨。塘边还有卷出新芽的蕉苗,等等。竹林还是苍翠的,发笋还得等几天。野草莓,开出了薄薄的黄色小花,太阳下金亮地闪着。但这一切,都压在了虫鸣里。
此间春阳,鸟语,花香,还兼以虫鸣,正适当于“明媚”二字。我想,没有虫鸣的林子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没有鸟语、花香一样。当我惊异于春日虫鸣之际,便掐指算算,“惊蛰”已过二十八天了。天地轮序,四季不欺,一切正当其时。这便是自然。
一番溜达,已近下午四时,便走向北门。一张“预约已满”的牌子,没有挡住鱼贯入园的人流。一廊如瀑的荼蘼紫花把我们拥出门来,花架下的迷迭草熏出诱人食欲的香气。算是游园的阑珊。
下完几级台阶,我们便泯然于滚滚市声之中。没有了鸟语花香,更听不到虫儿们的唱和。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