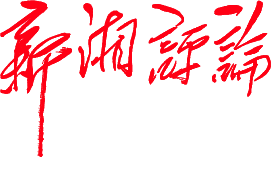伟人之初
——毛泽东是怎样被历史选择的(五)

毛泽东之初的启示
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的思想“站位”和党内地位
关于1921年到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整体上还是肯定的,并且留下了不错的记忆。他后来说:“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1921年至1927年,虽然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这个时期,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北伐时期,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
这段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道成长的过程,经历了“四部曲”。
第一步,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产物,走出这第一步,天经地义。第二步,国共合作反对帝国列强和封建军阀,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使然,走出这一步,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上的一次伟大觉醒。第三步,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这是推进和深化国民革命的必然要求。这一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及一些北伐军官的分裂。第四步,抓起枪杆子,明白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步是在国共分裂和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必然选择。
正是从第三步开始,毛泽东在认识上走在了党内多数人的前面,最终和比他大14岁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当了6年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分道扬镳。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当时对中央策略的批评,基本上是对事不对人,对陈独秀没有什么情绪化的言辞。
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的认识甚至走在了最前面。当抓枪杆子成为共识的时候,他的一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深化和定位了武装工农的意义;当武装工农成为共识的时候,他又明确提出了武装起来的工农应该到哪里去的问题:“上山”甚至可以去领导“土匪”。这就超出了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包括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央领导人的认识范围。这才有八七会议结束后,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而遭拒绝之事,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明确:我不愿意跟你们到上海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这显然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毅然转兵去罗霄山脉,落脚井冈山的伏笔。
开始走在时代前面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他此前并不以理论政策的论述见长。通常情况下,他被看成是一位善做实事而又有些执着的领导骨干。那时候,经常发表拥有理论深度和能够影响政策走向的指导性文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外,主要有蔡和森、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恽代英、高君宇……这样一些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有一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从1921年7月到1927年8月,只收了10篇毛泽东的署名文章。而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署名文章分别为26篇、17篇。中共初建时期急需要回答“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些根本问题。毛泽东作为实干家在党内地位沉浮不定,起落无常,是很正常的。
1927年以前,在党内中央领导层和决策层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陈独秀,此外相对比较固定的有李大钊、张国焘(一大以后)、蔡和森(二大以后)、瞿秋白(三大以后)等,1927年五大前后,又涌现出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陈延年、罗亦农、毛泽东、任弼时等一批敢作敢为,对党的决策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领导骨干。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从事过工人运动,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都是实干家,一个是军事工作权威,一个是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中心工作就在这两个领域,并且要将其融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和周恩来此后脱颖而出,也是必然的。
事情总是作始也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指挥机构还不能像后来那样发挥上下完全贯通的领导作用。对中央领导人在中央机关的工作要求,还缺少严格的规制。中共一大期间,怎么设置中央机关是有争论的,有人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政党,有人主张建立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党的中央应该是一个联络的机关,而不能任意发号施令。虽然在二大上制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决议案,强调革命党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才能保证有足够力量进行革命活动,中央和地方应成“严密系统”。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决议并没有得到严格落实和执行。
参与建党和党的早期成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有名的人之所以后来脱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把党建设成为什么样的政党上,有不同认识和诉求。像李达、陈望道这些对建党有重要贡献、后来虽然也没有改变信仰的早期党员,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党组织,恐怕就与不大习惯党内组织纪律的要求有关,当然也与陈独秀的个人领导作风有关。召开二大时,李汉俊有意不参加,但给大会写了封意见书,主张党的各地组织仿照联邦制,即使设中央,仅需1人即可。这样的观点在会上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二大后有一次在北大第三院开支部会,李大钊登台阐述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台下竟有人用脏话咒骂李大钊,“使得他立即退出了会场,后经调解,乃得平息”。广东支部的陈公博不顾中央与陈炯明划清界限的要求,与其走得很近,还公开发表文章与中央唱反调。在中央层面,还出现了张国焘“小团体事件”。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搞的党太松弛,要纪律严的党”。于是,联合部分干部组成小团体,意图按自己的思路改造党。马林在中共三大前也发现:二大以来的一年间,党的组织“很不健全”“党内同志间不断发生冲突,首先是党内组织了一个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国焘为首的‘小团体’,张把党员分为好坏两种,想通过这个小团体去加强党的活动”“党内中央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有4名是这个小团体里的”。为此,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批评张国焘的话,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错误。”也有党员干部把革命看作是热闹,看着谋个人前途之事,并不真心去实践信仰,比如周佛海当时收入较多,他为按比例交党费的事情而斤斤计较,结果是离党而去,这与陈独秀靠自己的稿费来维持党开展工作,境界不是差得一点半点。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力量来看,当时确实存在着“小党要改造和领导大国”这样的矛盾,党中央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派人到各地做某项工作或某个区域工作的特派员,中央领导层以及一般的中央执行委员,工作内容和区域经常变动。这是职业革命家的原本状态。这样一来,中央领导层人员的管理和议事规划,也不是很严格。毛泽东三大后被派往国民党内工作,还奔走于湖南和上海之间,常常不在中央;蔡和森由于对国共合作有保留,也不多问政策方面的事情,而是埋头写作不少文章;瞿秋白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忙了好一阵子,又放心不下上海大学的事务;张国焘没有安排上中央局委员,出去搞工人运动去了。中央确实有空心化之虑,但党员似乎也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常常只有陈独秀坐镇驻守,许多事情不经过会议由他决断就行了。即使开会,也多是谁在中央机关、谁方便出席,就召集谁来参加,由此形成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据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1926年准备北伐时,中央召开一个会议,“恰巧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两人反复辩论了几次,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国焘是他的学生,不敢回骂,声音愈说愈低,终于默然了。以此方法解决问题不止一次,这是陈独秀的缺点,因为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更明显的是五大上刚刚确立的领导层,由于形势突变,也不得不分散开去。陈独秀不再视事后,只得成立临时中央常委,5个人有3个被派往南昌去领导起义。于是在八七会议上又不得不成立一个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意思的是,派往南昌的3位常委,都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5月到8月上旬,中央领导就发生3次变化。
在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比较频繁,今天你来做,明天我来做,之所以是常事,还与先驱者们的信仰和情怀有关。邓小平晚年谈话中也曾说,当时的共产党人,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我们知道,陈延年是旅欧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但回国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周恩来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起点很高。在党内,1926年离开国民党舞台后成为陈延年担任书记的广东区委军事委员,后来受命到上海参加中央特务委员会,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而赵世炎是周恩来领导这次起义的重要助手。
一心做事,不在乎名利地位的作风,在早期党员骨干身上,比较普遍。比如,二大开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李大钊一直没有进入党的高层,只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在北京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八七会议上蔡和森等人不愿作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而推荐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的推让,理由都是要到外地干事;会后毛泽东谢绝到上海中央机关的邀请,一心要去领导暴动。可以说,这种情怀作风是党在创业时期形成的好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过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以前召开了6次),总共有170人担任过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人做过统计,其中有51位为革命胜利付出了生命,约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谈毛泽东早期在中共党内的沉浮,不能不有这样的视域。
- 新湘导读